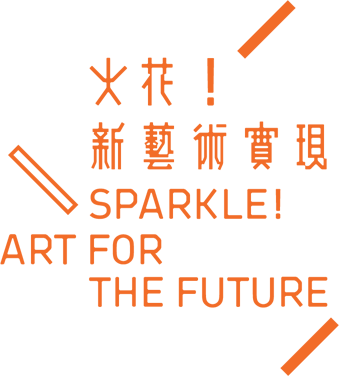以創作為事業 – 林東鵬
我有意識地以創作為事業,始於在學時期於工廠區設立工作室,以及零三年畢業後逃離香港的時候。
畢業的時候對畫廊運作沒有什麼概念,但因為創作的主要媒介是繪畫,因此比較容易被納入畫廊的體制。這並非有意識的選擇,只是環境、際遇。我們那一代(包括白雙全,李傑,周俊輝,關尚智等)由在學時期到畢業,只愛在工作室閒聊或盲幹,市場與專業的概念都是個人不斷踫釘的情況下,隨著大環境的轉變領會得來的。而各人對此的詮釋與應對也不同。
零三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獎學金支持下,我前往英國倫敦繼續進修。三年窮困的倫敦生活,我有幸遇上友善的畫廊。可惜是,這些友善的倫敦畫廊不久倒閉,聽說這通常都是友善的下場,不免惋惜,藝術界的運作也跟所有東西一樣現實。
說到賣作品,第一次賣出的,應該是小學二年級用過底紙複製漫畫,以五毫一份賣給同學。之後,就要數在大學二年級時,在學系走廊策劃的盒子展覽。同學都依相同尺寸製造木盒一個,將自己的作品放在其中,然後十多二十個盒放在一起展覽。當時的西方美術史教授收藏了當中幾件,包括我的作品。最鼓勵性的,當然要數畢業展覽時的繪畫作品《肉身》。當時我的指導老師陳育強教授暗暗地用了很驚人的五千元買下。這個「肉金」足夠我交十個月的工作室租金!他,總是無聲無息地幫助藝術系的學生。
畢業後第一次畫廊展出就是於專注香港藝術家作品的嘉圖畫廊。我的收藏家亦從當時逐步建立。零五年也嘗試在工作室與畫廊兩個空間同時展出作品,互補空間上對創作展示的不足。當個人漸漸在藝術圈活躍後,認識的人多了,認識收藏家的數目也多了,就希望合作的單位可以提供在展示及買賣以外的角色。 有時畫作還來不及被認真思考或展示,已被市場消費及忘掉了。 究竟是作品本身不具被思考或討論的質素,還是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,它跟本沒有這個奢侈的時間?對於我這個有時真太認真的人來說,還是我對這種模式心有不甘。 畫廊的設立與社會的制度,有時是對藝術家創作的挑戰。
從倫敦回來後,我的創作由個人遊學的孤寂情感,變成思考自身與其社會之間的矛盾與關係。這是在倫敦生活時蘊釀的。零六年回港,我簽約成為另一間畫廊的藝術家。除了之前累積下來的收藏家外,再有新的面孔。這其實是藝術家本身與畫廊兩者在不同層面活動下累積的成果。三年的合約為我提供穩定的生活,但同時在腦中揮之不去的是那份被消費的感覺。「被消費」並非在說作品買賣的問題,而是在買賣或展覽背後,藝術家創作的情況或往往值得探討的問題也未展開,就急不及待將其消費掉。對著畫廊、藝術館、雙年展時,我也不停問自己,若那是一種「消費」,怎樣才是好的「消費」。而那安穩的生活真的是我所需的嗎?
穩定的生活就如畫廊、國際雙年展、藝術館等,既可幫助藝術家也可扼殺藝術家。與生俱來的自省告訴我,是時候要脫離一下。我偶而/間歇從事藝術教育的工作,為的是想告訴畫廊「我的生活並不依靠你」。到我不再跟畫廊續約時,我也同時推卻了院校的兼職,前面彷彿無路可走。我創作了《從時間到時間》(Burger Collection) ,為我近年的繪畫作一個小結,並去了新界的鄉村義務畫壁畫。在沒有預計的情況下,在歌德學院作了一個展覽《過去進行式》。那是一個不可思義的展覽。一時之間幾個收藏家不單收藏了該批作品,還介紹了他們的朋友給我認識。這讓我肯定了,認真的收藏家是跟著他們相信的藝術家一起的。就在這個幸運之下,我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人,有跟他們合作,或自己策劃有關繪畫的活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