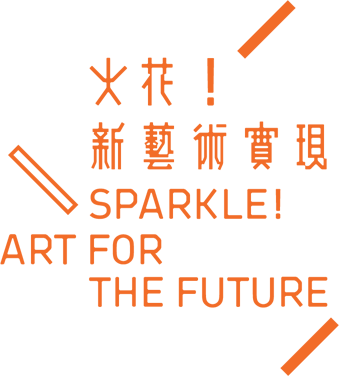我執筆墨
我執筆墨,能得前人樹蔭尋索己路?
◎ 阿三
中國風在近年國際藝術潮流翻滾多時,香港藝術家乘風而上;「後八九」回應當前中國獨特民風與社會變革的作品被消化得七七八八,聽說,「水墨熱」正在升溫,前景未明。香港,於現代中國史角色重要,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橋樑,亦是文化避難所。南來文人在殖民地疆土傳揚國學,迎接歐美思潮衝擊,翻新傳統中國藝術嘗試一浪接一浪。拋開既有傳統形式,以裝置錄像新媒體依然可以關懷中國文化,但學藝者發現舞筆弄墨經驗過癮鮮活,執意於此之上,他們又如何消化中國文化傳統,進入西方藝術論述?
嶄露頭角決執筆墨的香港年輕藝術家,不時被籠統地理解為中西兼容傳承中國書畫新一代。然而,我們有否發現在香港從事書畫創作的形勢何其嚴峻?我們又有否關顧這批以筆墨為根的香港年輕藝術家,需要怎樣的文化環境成長發展?
藝術思潮與其時代文化語境唇齒相依。中國封建制度瓦解,書畫傳統不能獨善其身,文人畫士大夫文化光環變得有名無實。在石屎森林上課的我們,認識歷代層出不窮的書畫潮流低頭瀏覽智能電話屏幕之際,或會心有狐疑,後感不甘。現當代水墨何去何從?文化城牆不容崩壞,但固守傳統只會不進則退。六、七十年代,呂壽琨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開講,由其學生編撰的《水墨畫講》一一紀錄其革新中國繪畫的理念,「元道畫會」及受呂壽琨影響的「一畫會」隨之組成。差不多時間,台灣現代水墨大師劉國松任中大藝術系系主任,替「新水墨運動」帶來新元素,「香港現代水墨畫協會」稍後亦成立。
「國畫」,相對「西畫」一詞而來,強調其文化傳統與媒材運用之異。按呂壽琨語,「水墨」確立於唐代王維;如今重提,實確欲距於「國畫」向內的意涵。「水墨」包含西方藝術觀念,現代意味濃,鼓勵自由創作,打正旗號尋索跟傳統不同的道路,又能在視覺及精神上對應中國傳統。「新水墨運動」不經不覺已是半世紀前香港藝術歷史一段,其翻動精神有多少留到我們手上?
後人有食?
尊古與師承,是中國藝術十分強調的內涵,跟西方叛逆不覊的向道截然不同。可是,王無邪在上世紀50年代已指出「國畫之逐漸趨於沿襲與公式化,使它與時代、環境產生非常明顯的脫節」,到底這特質是囿於發展的門柵,還是邁步前進的基石,的確要看各人造化。石家豪、管偉邦、鮑慕貞,或年輕一點的徐沛之、賴筠婷、梁依廷、蔡德怡及黃向藝等,相信都是後者的代表。
賴筠婷《遊客》(局部),175cm(高)x 85cm(闊)厘米,一套兩件,水墨設色紙本,2013尊古,簡單而言即能從作品本身清楚體現藝術傳統的某些脈絡。這是知識層面的論述,亦是日積月累操練得來的技藝。用毛筆鈎線「畫公仔填色」的工筆繪畫,是題材沒經提煉及技法單薄的反面例子。需時的「浸」(淫),是普遍認同得到一定水平的不二法門。不是說資深老手定得優勢,但剛學筆墨不久的初生之犢,多有待行內「世叔伯」肯定。
師承除對應藝術史的「路數」,亦可能指向跟誰學藝的背景。老師善於繪畫翎毛,學生也離不開水鳥鳴禽創作,這現象在國內美院亦頗為常見。創新,其實淺白得可能只是把書畫與現代生活距離拉近,惟此想法如同踩上鋼線,必先敬古人頌師長,而後在未知多大的範圍加入個人元素。結果是失足跌墮損手爛腳,還是安全抵達彼岸繼續走自己的路,得看命數。「後生仔(女)貪得意」或「雕蟲小技」是常聽到前輩對創新的批評,文字媒體亦不自覺地成為共謀以「反叛」形容敢於嘗試的年輕書畫家,真不知應該多謝還是「多得佢唔少」。設立獎項鼓勵具潛質新秀投身創作的態度,通用於各藝術界別。但香港當代藝術獎(或舊稱「雙年獎」)年輕書畫家獲獎,可喜之餘亦憂心忡忡,頒獎禮開幕當晚,得俾定心理準備隨時迎接前輩酸溜溜的冷言冷語。師徒可成創作路上有情有義的知音伙伴,但純粹因為「道不同」而成陌路人的,也親聞目睹。
鮑慕貞《肖形印.瑜伽系列》
生生而不息?
鮑慕貞的《肖形印.瑜珈系列》把尊古與創新拿捏得四平八穩,面面俱圓。她個人近年定時參與瑜珈運動,把「拱式」、「樹式」等姿勢造形結合個人心神領悟,體現於篆刻的三法之上,恰如古人遊山玩水後透過紙上筆墨重現心境。這種有感而發的創作原點,無獨有偶見於徐沛之的書法創作《人生三部曲》中。行草飛疾筆力與扇面形式均向古人借來,但觸動三十來歲香港仔的,正是陳奕迅的流行曲《單車》、《葡萄成熟時》及《沙龍》。國學傳承任重道遠,誠然,我們需要更多新力軍的青春注入。畫會書會人頭鼎盛,但書畫界斷層問題是不能否定的事實,氣候氛圍及其潛規則是人才去留與成長的關鍵。
中大藝術系一直堅守中國藝術教育崗位,舊制度下書法基礎、國畫基礎、山水、花鳥、人物均是獨立科目,而書法史、繪畫史及中國藝術史專題則鞏固學生的知識根底。即使,近年科目重組改革,學生仍有一定時間專於中國藝術。成立未到十年的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,四年學制下學生在第三、四年才專於視覺藝術課程。而現時規定,學生要在26節課堂學曉山水花鳥人物工筆寫意,倘若他們選修的話。難怪乎有戲言說,這是專業一點的興趣班而已。新一代需要友儕相長,需要識貨的聽聆對象分享興奮渲泄苦悶,才能舒懷吐氣,而我們的創作路才不至寂寞。
徐沛之《人生三步曲 「單車」、「葡萄成熟時」、「沙龍」》,30cm(高)x 50cm(闊)
一組三件,水墨紙本扇面,2013
打造文化環境
資本主義遊戲規則下的國際藝壇或市場,均以西方為對話對象。中國藝術是種吸引外國人的文化身份象徵,能連結傳統藝術內涵又具備讓外國人讀懂的元素的水墨作品,能流通於各大小展場或買賣平台,故最為吃香。獲他鄉認同,不代表裨益本地文化討論。市場,是不會以中國藝術角度觀看作品;而展覽,又能否以中國藝術脈絡與視角觀看?我們實在十分需要具深度的論述,如趙廣超重尋被視為國畫最高標準「氣韻生動」乃「鑑賞心得」而非「創作法則」。我們又十分需要開明而敢於越界的前輩開山劈石,如已故翟公翟仕堯1996年應Cosmopolitan邀請創作人體書法作品。「新水墨運動」既詩意又務實的「東夢西尋」討論向導,是時候再啟步再;類似去年香港藝術館《原道》展覽及其國際學術研討會,也得持續開展。
歷史不是抱進棺材的家檔。我城身世朦朧,現卻漸露輪廓。呂壽琨早已提及「香港隨時間所建立的文化藝術,必隨地區的存在而存在」。香港文化環境有別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社會,此福地的文化主體如何體現,千禧過後屬於本土的新水墨模樣又何以形塑?